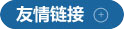被称为艺术史界“捣蛋鬼”的徐小虎,今年已经91岁了。她是中德混血,生于南京,后来又在重庆、上海度过了青少年岁月。在中国的这段生活经历,培育了她日后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浓厚兴趣。
数十年的沉淀,徐小虎已是著作等身,开创了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。但回过头看,她的学术和人生之路走得并不容易。最近,徐小虎在尼泊尔接受了“Green BAZAAR”的专访,回顾了她作为学者和女性的一生。
她的一生都在与虚妄做对抗。她揭开山水画的真伪,却换来学界的争议与冷待;她在婚姻与身份的桎梏中挣扎,直到暮年才真正属于自己。她的人生是一场壮游:在炮火中出生,在迁徙里长大,20岁就被推入一段荒谬的婚姻,跪在厨房的地板上写论文,独自面对古画的冷光,也在尼泊尔的山谷里与云雾对坐。
她说:“没有地方是我的家,大自然才是我的归属。” 九十多年走来,她把孤勇与求真写进历史,也把自己交还给自然。
限时五折,精彩好书,不要错过❗️
展开剩余93%“没有地方是我的家,大自然是我的归属”
尼泊尔的山风在午后变得格外轻快,像是翻开画卷的手,拨动着森林深处的暗影。徐小虎端坐在竹椅上,背后是绵延的喜马拉雅余脉,云雾缠绕山腰。她一身白色长衫,利落的微卷短发,脸上虽有沟壑,但紧致不见松垮,说话丝毫不带间断,难以想象眼前的她已经91岁了。
在艺术史的世界里,徐小虎一生都在与“真伪”缠斗。因直言中国山水画的真伪存疑,她遭冷待、被排斥,甚至错过整整一代学术场域。她的婚姻与学术都曾为外力所役,直到暮年,才终于属于自己。78岁那年,她离开尘嚣,走进尼泊尔的山谷。十三年来,她不通语言,也无邻里往来,却在这里收获比故乡更深的安顿。
1934年生于南京的徐小虎,童年是在炮火与迁徙中度过的。当日军轰炸南京的警报响起,母亲带着她逃往德国,后又辗转意大利。在罗马大使馆的花园里,一棵无花果树成为她第一个隐秘王国。“它是非常包容的,”九旬的她回忆时,眼底仍闪着孩童般的光,“穿着硬邦邦的小皮鞋爬上去,折果子,在树杈里一待就是整个下午。”那时她不懂这叫冥想,只记得这种被自然轻轻托住的纯粹的存在。
8岁回到硝烟弥漫的重庆,飞机降落在泥泞的跑道上。徐小虎刚一出来,就跪下亲吻了大地。“破破烂烂的机场,脏得不得了的泥巴地,我却激动得不得了,这是我的祖国、我的父国,感激感激,我回家了。”她家住在八块田13号,要从歌乐山下的磁器口坐滑杆上去,经过一个停车场再走半个多钟头,一间丑丑小小的黑屋子出现在眼前。屋里光线昏暗,没有电,也没有自来水和马桶。屋外上方是两层楼的白色房子,是邻居有钱人王家的住所。
到家时,奶奶站在阳台上急切地等待着。她第一次见到父亲跪下,和奶奶相拥而泣,夹杂着徐州话的哽咽。母亲是德国人,带着妹妹在一旁忙着收拾行李。屋里杂乱无章,行李散落,徐小虎一个人进去,看到大圆桌上有壶茶。她端起茶杯,一口口喝下,虽然极苦,但想到这是祖国的味道,是同胞喝的东西,她便自顾自地喝完了整壶茶——这是她最初的归属感,也是她性格里倔强、敏锐的根源。
那天晚上,油灯微弱地照亮房间,蚊子多得惊人,虽然和意大利宫殿式的居所天壤之别,她却只想脱下身上的西式服装,脱掉亮亮的小皮鞋,像大家一样穿斗笠、草鞋,在黑暗中享受自己的土地。“我爱死了,这个又穷又脏又没有电的地方!”
刚回重庆时,徐小虎一句中文都不会,只能从一年级重新开始。入学第一天,她拼命记下老师教的“来来来,好好好,大家来上学”,小鸭子儿歌至今还能唱起。母亲担心她忘了德语,逼她用德语念格林童话,她却执拗地翻译成中文。
在歌乐山的避难岁月里,徐小虎找到了第二处圣地——松树下的方石头。坐在那里俯瞰山下远远小小的嘉陵江和沙坪坝,穿黑布鞋的脚踩着雨后散发清香的泥土,耳朵装满叶子“谈天儿”的细语。这种体验刻入骨髓,以至于后来在上海生活时,她常在清晨哭醒:“枕头湿哒哒的,太想念歌乐山的自然天地了。”
这种对自然的归属感,贯穿了徐小虎的一生。后来她在牛津读书,窗外是阴冷潮湿的英国天空;在中国台湾生活,夏季的暴雨如注。但无论身在何处,她都在寻找“那棵树”的影子,那个隐秘的居所。
可在自然之外,现实却筑起层层围城:婚姻的绑缚、学界的冷待、人情的起伏,都曾让她摇晃。她从幼年漂泊,到20岁前被推入一段不对等的婚姻;从厨房里跪写论文,到山水画的鉴真发现被主流学术圈冷待。所幸的是,自然始终庇护着她,使她在重压下依然挺立。
尼泊尔是她最后的归宿。年近八旬,她放下艺术史研究,远离城市喧嚣,住进了加德满都的山谷。这里树与树保持着“自然的距离”,有着“城里找不着的放心和自在”。她常感慨尼泊尔人大概是世界上最穷却又最快乐的人群。他们常常工作了四五个小时便会放下工具,“今天赚的钱够了,我们去生活了。”在徐小虎眼里,尼泊尔人懂得以心连接天地——当一盘水果被高举过头顶奉给神明,“整个灵魂就上去了”。
在这里,她放弃了最爱的生鱼片和酒,笑说,“看到你们活着,我比吃生鱼片还开心,这份快乐让我彻底解决了不吃肉、不吃鱼的问题。”但偶尔也会有忍不住的时候,心脏病限制了甜食摄入,她却会假装不知道般偷偷分食蛋糕。当你提醒她时,她狡黠地眨着眼回道:“所以我只吃半块。”
年过九旬,当视力衰退到需要放大镜叠加眼镜看药瓶说明时,徐小虎计划用朗读软件继续接收讯息。她自律地保持着每天1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,而在90岁之前,这个数字是16,她习惯每天从各个渠道大量摄入信息,采访间隙也会分享一些国外看到的八卦新闻与我们闲聊。年轻时的她走路带风,看到如今自己走路喘气,又有些生气。面对衰老,她带着些许抗拒却也坦然接受,“感谢我享受了那么久的(生命),身体做了九十年,有点累很正常”。
如今回望,徐小虎坦言这一生都是reaction(反应),没有任何planning(计划),她被命运的潜流带向一个又一个未曾预料的渡口,每一次剧烈起伏的冲撞,最终都在山风云雾里悄然平复。九十多年走来,她依然会在午后的山风里体会到静谧,在树藤的环绕中感受到安宁。她说:“没有地方是我的家,大自然是我的归属。”
原来我也可以有我的phD
在一次访谈中,徐小虎说过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提醒:“如果有男人对你说‘没有你我活不下去’,快跑!”这看似调侃的玩笑,却是她用七十年的人生才得出的答案。
1951年,17岁的徐小虎踏进本宁顿学院,自由如空气般流动:无人监管的选课,走廊飘荡的即兴诗歌与琴声,宿舍里小酌与恋爱的气息。她仿佛置身于一个无限延展的世界,她画画、唱歌、加入乐队、登台表演,沉溺于纯粹的创作世界。毕业时,她的作品五花八门:一堆短篇小说、一次绘画与陶艺展览,还有一个物理实验装置——威尔逊云雾室,用来观察电离辐射路径的粒子。年轻的她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问下去、一直创作下去,她梦想成为话剧演员,在剧场排练室挥洒热情。可是生活很快像一阵冷风,吹灭了她以为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焰——那个荒谬的转折,骤然让自由的畅想变得脆弱而遥远。
她的导师,58岁的瑞士音乐家保罗·博普勒,忽然向她告白。她吓坏了,几乎落荒而逃,甚至从美国东岸躲到了西岸的姑父李方桂家里。她去信给保罗:“我不想恋爱,不想结婚。我只希望26岁以后再考虑男朋友的事儿。我最想做的,是去欧洲学戏剧,搞一个流动剧团。”那一刻,她是清醒的,也是坚决的。
可命运比她的拒绝更暴烈。一天深夜,佛蒙特州的电话打来,保罗在另一端袒露:“皮蒂(保罗的妻子)离开我了,带走了孩子和钢琴,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请你嫁给我。”这一声哀求,成了铁笼。19岁的徐小虎,被拽进了58岁男人的空屋子,成了全校最年轻的妻子,住进教职员宿舍,成了他人眼里既被排斥又被同情的存在。
“Ridiculous!太可笑了。”多年以后,她仍会摇头苦笑:一个已婚三次、带着两批孩子的老男人,怎么能要求一个尚未涉世的少女做他的妻子?
“我活了七十多年,才彻底明白:那是不应该的。”她的声音忽然尖锐起来,“可笑的是,我当年竟觉得,如果嫁给他能让他快乐,他就能去做音乐会,带四千人听到那些古老的乐章——那我为什么不呢?我的付出很小,大家的收获很大。我当时觉得是自己成全了世界。”
这种“为别人”的逻辑,延伸到她的整个早年婚姻。丈夫攻读博士,她就随行做助手、写讲义,甚至在厨房的地板上跪着誊写自己的论文,白天做家庭主妇,夜里再偷偷恢复成学术的自己。她后来讽刺地说:“我为了这大男子主义的游戏,我贡献了我的青春、我的生命,去成全他们的成就。”
可这一切换来的,却是她的自我长期隐没。她自己真正的戏剧梦想,被搁置;她的学术才华,在男权体系里被驱逐。1955年,她生下第一个孩子;1971年,第五个孩子降生。那时刚好有了避孕药,从此她才可以选择不再生育。直到牛津录取信寄到,她才第一次意识到,属于她自己的道路并未被彻底掐断——“原来我也可以有我的PhD(博士证书)。”
觉醒始于58岁。当第二任丈夫索要他的“自由”时,婚姻的算式忽然清晰:要么三人痛苦,要么两人解脱、一人承担。她选择了后者。签字的笔落下,并无想象中的狂喜,更像一种平静的成全。之后她行走于希腊与中亚,追寻西周青铜器纹样的源头;在俄国冬宫轻抚塞西亚金兽,解开动物纹饰的秘密;在爱琴海岸比较古希腊陶盘与西周青铜器的器耳的曲线。
每一次观察、每一次触摸,都让她后知后觉地意识到: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。婚姻的解体,并非自由的瞬间迸发。它更像一把钥匙,缓慢旋开一道门缝。门外,是她阔别已久的学术疆域。她终于能把所有气力,都摁进真正属于自己的泥土里。
91岁回望,徐小虎把两段婚姻说得冷静而尖锐:第一次,是“补洞”——填补老教授的情感空缺;第二次,是“育儿”——照顾比自己小九岁的丈夫。她终于承认,那些年都是误入,都是为别人而活。
可人生并不会在顿悟后归于寂静。在尼泊尔的修行让60多岁的孩子们越洋质问徐小虎:“You abandoned us,mum(你抛弃了我们,妈妈)。”她陷入回忆,却又当即辩驳:“或许他们8岁时,我给的爱不够……可我也是十五六岁就离开了我母亲,我就没有再依靠她,你们还在依靠我吗?你们都60多岁了还在和我吵‘你爱不爱我’?我的父母从不拥抱亲吻孩子。他们忙着社交,我们是佣人喂大的。而我亲手给你们做饭、哄睡、送学——我做得远比他们多!”
尼泊尔的云雾逐年浓重,隔开了血缘的噪音。父母、姑姑、弟妹、早逝的女儿,都退成相册里的淡影。徐小虎不再需要向谁证明“够不够格”,只需守住一种清澈的自洽。她对女孩们的告诫,最终也成了给自己的祝祷:“你的责任,不是伺候别人,不是去填补男人的空缺。你的生命生下来,是要完成你自己的目的。”
被遗忘的真迹
1960年代,徐小虎跟随当时退休的前夫暂居普林斯顿小镇,家门口就是普林斯顿大学。在一次旁听课程后,她随意地翻着课程目录,眼睛忽然停留在了字母“C”开头的“China Studies”下,这让她想起自1951年去到美国后再未说过的母语,再往下看第一行“A”开头的Art——“这简直梦想不到的棒!”
36岁的她抓起电话,即刻报名。面试时,教授见到她,以为她志在“landscape painting”(山水画)。不懂的徐小虎误判成是外出写生画风景,可实际上,她面对的,是完全陌生的艺术史学术世界——二手文献、材料分析、晦涩的术语,这与她在本宁顿学院时的经验大相径庭。
初遇艺术史,她觉得“吓死了”。她不懂什么叫“史”,只觉得那是一群“死人”的东西,与艺术家对话几乎不可能。但正是这次误打误撞,成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向。
艺术史系的幻灯片室昏暗如洞穴,当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的影像缓缓在幕布上呈现时,徐小虎的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下——“那座山(像)是歌乐山的爷爷,让我仿佛看到了神,有一种形而上的大尊敬”,多年后,她仍会用带着颤抖的语气回忆那一刻。那是她第一次在学术研究与古画之间建立精神上的联结,她开始寻找一种区别于主流的突围路径——用感受去触摸画的灵魂与时代。
然而,这种方法并不被接纳,甚至激发了徐小虎与导师方闻教授的矛盾,对方甚至扬言让徐小虎“一辈子无法在这个领域工作”。冲突骤然升级,徐小虎的普林斯顿学习之旅也因此被迫终止。
离开课堂,徐小虎转向实践的现场。每周她会搭51分钟的公交车到纽约,在王季迁堆满卷轴的公寓里追问笔墨的奥秘。这位横跨收藏与鉴赏的大家教她如何感受中国山水画的笔墨韵律,有次王季迁拿出两幅画让她辨优劣,她选了“有鸟的那幅,因为有趣”,结果被笑“不懂笔墨”。她反唇相讥:“我选不出来,是我笨;可你解释不清,不更笨?”这场持续八年的追问,成就了《画语录》的经典对话。
王季迁把“笔墨”比作京剧演员的“嗓子”,要求徐小虎不能只看题材的热闹,而是要听那条隐形的气脉与功夫。后来,徐小虎把这种感知再度翻译给年轻人:“抛开知识,用皮肤的触感‘听’画,打开细胞——像听音乐般感受笔墨的生命律动,体会它在‘纸’上行走的快慢与轻重。这便是倾听那‘看得见的灵魂的声音’。”
离开美国后,徐小虎在中国台湾度过了她最孤独,也是最炽热的一段岁月。1970年代,她频繁走进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库房,一卷卷调阅古画。台北故宫每天可以提15张画,那一年徐小虎去了6次故宫,她戴着口罩、手套,将一张张珍品放于眼前,但品鉴后的发现却令她如坠冰窟:董源名下无真迹,范宽真迹仅存一幅,马远、夏圭全是伪作。唯一令她震颤的是马麟(马远之子)的《芳春雨霁图》:“鸭子凫水的动态,每一步可踏入的空间,湿润的空气感——这才是南宋真魂!”
回到家后,徐小虎高烧三日。她意识到,中国书画史问题不是大师的名下有没有假画,而是大师的名下没有一幅是真的。这发现直指艺术史根基,但她紧握冰冷的真相,未曾动摇。
1981年,徐小虎在台北完成了对于吴镇书画重鉴的报告,因为用的是在普林斯顿学的结构分析断代法,她将报告寄给方闻教授,希望将此作为博士论文。但回信冷冽,她的请求遭到了拒绝。
然而这并不能阻断徐小虎的求真之路。50岁时,她带着牛津大学的录取信跨越大西洋,把在台北故宫的发现转化为学术武器:她提出“结构分析法”“笔墨行为学”“母题演变”的“三法”,力图以科学的方式为古画断代。1987年,她发表了博士论文,指出吴镇的真迹存世极少,而乾隆钤印的“神品”多为明代仿作。当时台北故宫的新院长警告她:“你说我们有假画,你的作品我们绝不支持。”徐小虎失去了在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与调画的资格,伴随而来的是学界集体沉默,只有老友高居翰与她“只谈心不谈断代”。
1995年,基于徐小虎博士论文的英文著作《被遗忘的真迹》出版,唯香港大学出版社敢接手。彼时她在台南艺术大学教书,带学生用“三法”重鉴古画。有学生发现文徵明的真迹只有两幅,但在论文答辩时却被警告:“不能发表,会被攻击。”她鼓励学生出国深造,但无人敢行,“他们都转了行,有的搞当代艺术去了——那里没有真假问题。”
2012年,《被遗忘的真迹》简体中文版出版,78岁的徐小虎突然收到内地三个学术机构的邀请,在后续的采访中,她把这个机遇称为“奇迹”。参加上海博物馆的会议时,徐小虎与老学弟傅申一起坐在首排,询问参加的与会者为何都比他们年轻,“上次开会时,站在台上的老师们都比我们老多了啊!”在傅申的提醒下,徐小虎才惊觉自己已经三十多年没收到过学术会议的邀请,跳过了整整一代的学者,反而成为整个会场里最老的人,“又可悲,更可笑”。
徐小虎一直期待,在她的论断被更多人看到后,某一天信箱里会多出一些来自陌生学者或是学生的邮件,讨论山水画的笔法或断代,无论是驳斥、反对还是赞同,怎样都可以。可直到今天,这封邮件从未出现过。话音落下,拍摄现场陷入沉默,任何应答在残酷的现实下显得分外无力。
她始终惦记着要编一本真正的“真迹集”。在她眼里,这并不是野心,而是一份责任——要让后人能清楚地辨认哪些是少有的存世真迹,哪些只是赝品。可这个愿望始终未果。
在转天回程的路上,再次谈及山水画时,她语速渐急,藏不住的愤懑。“大家有两只眼睛、两只耳朵,可就是看不见真实,听不见真话;明明(画的)“骨肉”是真的、假的那么明显,他们却宁愿视而不见。”
她反复拷问自己:“徐小虎,你觉得你那么棒,你看到了,别人就必须看到吗?如果一座房子着火了,你看见火焰,难道不该去把他们拉走吗?”然而残酷的现实是,大多数人宁可站在火前也不愿挪动脚步。“这么明显的真实,大家不看,或者看见了也不愿意做什么。”
但她从未因此而放弃“说真话”的勇气。她说,若外星文明来问人类艺术成就,我总得交得出真东西——“我对那些已故的大师们有责任,得说清哪些是他们手笔,哪些是挂名侮辱。”
她一生所守,正是这份对逝者的责任——对哑默的历史,对那些无法辩白的灵魂。
尼泊尔的云雾聚了又散,徐小虎的故事像她珍视的《雪竹图》一般:一块伟大的碎片,透射着未被世俗化的凛冽光芒与生命韧性。她的战场归于寂静,但那些被质疑的画作、被颠覆的定论、被重新定义的“真”,以及一个女性最终寻回的完整自我,都在寂静中获得了自然的回响。学界的笔墨之争未息,但她已行至彼岸:那里无须署名,万物皆是宇宙的手笔,而真实,是唯一的落款。
限时五折,精彩好书,不要错过❗️
🎁
、
发布于:北京市